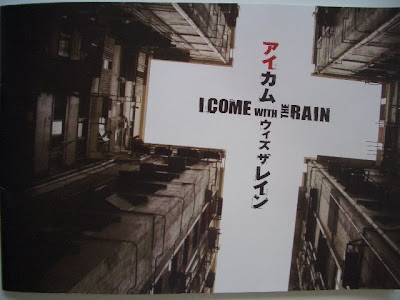不同的人對於越南的映像是不同的,在法國“情人”的記憶中,它是頹敗的橡膠花園,是在紙醉金迷中春風沉醉的異國愛戀;在美國“野戰排”的記錄裡,它是殖民者優越目光下貧窮、飢餓、混亂、愚昧的國度,同時也是讓無數年輕的生命永遠沉睡的難以擺脫的夢魘……而在陳英雄的影像世界中,越南則是“青木瓜的香氣”、 “三輪車夫”的忙碌以及濕熱多雨的“夏之滋味”。
《三輪車夫》是一部奇特而迷人的影片,沒有《青木瓜之味》中的清新溫婉,也沒有《夏天之滋味》中的純粹優雅,陳英雄第一次懷著某種清醒的痛苦和傷感的詩意將焦點聚攏到越南下層社會殘酷的現實之上:貧困、暴力、性變態、死亡以及伴隨而生的熨燙、陰鬱和狂躁。但是,陳英雄對於傷疤的揭露並非那種強者對於弱者居高臨下的“撫慰”或“環視”,而是作為一個生在越南、長在他鄉的具有雙重文化身份的電影人自我刻畫的真實表露。因而《三輪車夫》從整體上呈現的是一種紛繁而交錯的藝術氣質,在現實主義的畫面背後有浪漫主義的真實記憶,在西方化的創作思維中蘊含著濃烈的東方情結,在世俗城市雜沓凌亂的精確凝視中又滲透著哲思般的詩情訴說。可以說,在“後殖民主義”的語境中,《三輪車夫》最集中地體現了陳英雄在西方/東方、話語/本土、他者/真我等二元對立的糾葛中,渴望通過容納互補的彈性思維去消解“對抗性”顛覆立場的創作思維。
一.沒有名字的漂浮影像
在越南,人們認為他是法國人;在法國人們又認為他是越南人。作為一個法籍越裔導演,陳英雄的身上不可避免地接觸和負載著兩種或多種異質的文化傳統。一方面,他的影視理論、表現手法和命題背景是西方化的;另一方面,他悠遠恆久的民族記憶、深層次的懷鄉意識,以及個體在現代化城市中漂泊無依的生命體驗又是東方化的。因而在面對自我、面對故土時那種被藝術的理性和歷史的責任所分割的痛徹的關注與美麗的想像使得他的影像瀰漫著某種多元而深沉的氣息。他的電影中總是會出現太多的並置,平和與焦慮、美麗與傷感、現實與回憶、表現與沈默、西方的生命意識與東方的宗教靜悟,等等。可以說,他在創作情緒上的複雜膠合與意識層次上的關切追問是他游離於相對立的兩極又無法真正融入到任何一個類別中的文化身份決定的,是已經深深融入到個人的生存記憶與身份認同中去的。因而,陳英雄所表現的世界是沒有名字的、漂浮的影像,他既沒有以一個完全的“他者”身份對自己的鏡頭作“後殖民式”的加工,也沒有以一個放棄藝術甄別的弱勢文化捍衛者的身份去構建那種封閉獨立的神話或意想,而是以一種淡然釋意的姿態去尋求某種,至少是暫時性的大同與包容。而這種情緒在《三輪車夫》中顯得尤為明顯。
影片所講述的大多是一群沒有名字的人,車夫、詩人、老闆娘、姐姐、妹妹、爺爺……所有這些人物在陳舊而雜亂的胡志明市街頭相互交集,就像是河流上流浪的浮萍在某個濕熱的夏天尋找生命的歸宿,沒有確切的時間敘述,也沒有清晰的空間關聯。這種無名的設置本身表明了導演試圖超越一個生活記錄者的文化身份。
不過,陳英雄對於殘酷現實的還原是大膽而凌厲的,極富表現主義的手法一次又一次地將那些觸目驚心場景呈現在我們面前。車夫為逃避警察從下水道走出時的驚恐死狀;黑幫老大用尖刀劃破對方喉管時的殘忍,以及後面屠宰場殺豬時血流噴湧的鏡頭疊化;迪廳裡尋找醉酒客戶時燈火急閃的狂亂;無能的嫖客要求姐姐喝水並站立排尿的變態;車夫偷運毒品時像一扇豬肉般突然橫飛於眼前的死屍;攻擊偷車人時釘在木條上的眼珠;在過曝的色調中迷亂的車夫將油漆澆滿全身,並在紮緊的塑料袋中掙扎呼吸的臉部特寫,還有被含在口中不停搖擺的壁虎尾巴和金魚等等。所有這些場景都充斥著血腥和暴力,並給人以驚恐不安的感覺。毫無疑問,《三輪車夫》的情緒表達和影像塑造是直接而逼真的,在這裡,溫情的面紗被無情地割裂,堅忍與暴戾,希冀與絕望,掙扎與遊走,所有的情愫都在刺眼的白光和凝重的血色中變化無法凝視。
但是,儘管如此,陳英雄並不是一味地去揭示殘酷、暴力和苦痛,即使是在反映社會的罪惡與墮落,他的鏡頭中仍然表現出某種陰鬱的詩意和殘酷的美感。憂鬱而傷感的歌聲,平靜而抒情的詩歌,車夫一家齊集一堂的溫馨與關懷,妓女們相互打鬧嬉戲的簡單和快樂,站在歌廳裡嫵媚而動人的姐姐,如銀色雕塑般美麗淡雅的檳榔棕櫚花,以及車夫最後載著家人載街頭穿梭時的滿足……都讓我們感受到一種潛藏於畫面背後的堅硬力量和精神質感。事實上,導演那種詩意化的表達方式始終貫穿著整個情節的進展,就算在表現罪惡與殘忍時也不例外。車夫從下水道逃出後把頭放進魚缸裡清洗的鏡頭在充分錶現人物的迷離和現實的無情同時,也隱隱地表現出一種人性因恐懼與無助而自我麻痺並慢慢腐爛的墮落之美。泥土、金魚、水草、小蟲,污垢,在那有力而簡潔的切換中彷彿一支溫柔的利箭射向觀者的心頭。詩人解決變態嫖客的那場戲,陳英雄也表現的干淨而沉重。沒有大聲的嘶吼,沒有激烈的打鬥,一切都在嫖客痛苦的表情、掙扎的動作以及詩人平淡的注視中默默進行。而長滿雜草的樓頂,,抑鬱躁動的氣氛,灰藍陰沉的色調,在映襯出詩人內心的仇怨和自責時,也投射出一種靜默的道德意識。這是他唯一一次為了正義而殺戮,當他點起捲菸站在沿邊注視著身下破敗的街道時,一種靈魂解放後的釋然和平靜不言而喻。另外,開頭那位嫖客在第二次“光顧”姐姐時的場景也在細節的精緻展現中變得溫柔而優雅。所有這一切都反映了陳英雄在面對故鄉時所擁有的複雜感受,在尖銳凜冽的視覺呈現中給予生命一種公正的判斷,那是面對慾望時的徬徨,經歷殘暴時的震驚,自我麻痺時的迷亂,以及靈魂清醒時的痛楚。
當然,陳英雄並沒有放棄希望,無論是曾經迷失的車夫,還是淪為妓女的姐姐,又或者是販賣靈魂的詩人,最終都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歸宿,找到了那個消失已久的人性:老闆娘的兒子用生命償還了母親的罪孽,同時也換回了她的良心;三輪車夫在老闆娘的幫助下又開始了蹬車生涯,雖然平淡卻很幸福;詩人在烈火中完成了自己最後的救贖,隨著遙遠的記憶和過去一起實現了靈魂的返航;而姐姐則呆在廢墟中默默地守望著,或許是在欣賞一種殘酷的美,又或許是在緬懷對於詩人的那一份真實。經過這一場時空的輪迴,陳英雄以一種自省的方式為影片中的人物找到了富於東方色彩因果式的回歸和拯救,審慎而堅定。而結尾處車夫臉上洋溢的自足之情以及那些在歌聲中充滿生氣的孩子則表達了他對這個國家和民族潛藏的力量以及美好未來的一種希望。
陳英雄正是通過這種在多元層次中漂浮的影像,在一個相對含糊而開放的情節延展中,以精緻而不失本真的鏡頭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殘酷卻充滿希望與活力的越南,並依靠這些鮮明而提煉的影像符號表達了對於那塊飽含著苦難、淚水和絕望的土地最為詩意,也許也是最為卑微的敬意。
二.“失父”與“尋父”
影片中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在壓抑和苦難中無奈地沉淪,既無法逃避不堪的現在,又不能忘記沉重的過去。儘管他們可能有著各自不同的理由,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那便是“父親”的缺位。而《三輪車夫》事實上正是包含了這樣一個母題。
影片一開始,我們聽到的便是車夫父親的聲音,“孩子,你聽著,我們家一直靠蹬三輪車為生,從早到晚,必須要不停地蹬車,才能糊口,吃、睡都得在街上,腰經常會疼得無法起床,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根本沒什麼前途,到死也不會給你留下什麼,所以,你得好好想想,去試著找找更好的路子。”視覺上的缺失並不意味著不存在,生命的終止也不意味著靈魂的消散。影片開頭父親的話語既帶出了後面關於蹬車生涯的情節描述,實際上也交待了車夫後來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內在動因。作為一個偶然的“陰謀”,三輪車被搶剝奪了車夫賴以謀生的工具,但也在另一方面為他提供了一個另尋出路的機遇。在帶著害怕的心情放火燒了糧倉以後,車夫在接受同夥對於其行動大膽而果斷的吹捧時,表現出了之前難得的自信和歡喜。他向詩人提出,想要加入幫會,想要成為和他們一樣的人。在他眼裡,加入一個勢力強大的組織或許就意味著找到了父親所說的出路,意味著得多的錢和更強的力量。最關鍵的是,對於一個飽受欺壓的懦弱的人而言,投入到某個有力的組織相當於找到了精神上的父親,找到了心理的寄託和安全感。這裡,“父親” 的缺失和不在場的“在場”成了情節發展和人物塑造的動力。車夫在幫會中成長是迅速的,他用縱火通過考驗,也學會了識別和使用槍支。當他再一次與搶車人在胡同里相遇時,他果斷地選擇了復仇,這是他力量增長的一個佐證。但車夫在本質上是善良的,他會在犯案逃跑時別人的落水而停留,也會為老大殺人如殺豬般的技巧表演而驚慌,特別是在運送毒品中目睹了一個鮮活的生命如何突然間像新鮮的豬肉一樣倒在自己的三輪車上時,一直被夢想或者說父親的“偈語”所掩蓋的恐懼在他心裡翻騰,他開始了揮之不去的噩夢,而事實上他僅僅只是目睹了別人如何殺人而已。
當車夫從噩夢中醒來的時候,我們聽到的卻是詩人的聲音:“爸爸/你犧牲自己/是為了救我/今天早晨/我感到分外寧靜/彷彿活在你的體內/彷彿活在你的輪廓/步伐和舉止之中那嶙峋的指頭/那粗糙的雙手/是你的還是我的呢/我的臂彎感受到你肌肉的關節/你的皮膚被灼得粗糙了/經年抵抗酷熱嚴寒/你把血脈喚作人生的路途/現在我恍然大悟了”。在詩人的吟誦中,我們知道了車夫的覺醒,他決定離開他曾經嚮往的生活,意識到也許在灼熱的太陽下蹬著三輪車可能更安全更踏實。當然,想要從惡夢中逃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吟詩的詩人實際上也處在“失父”的狀態中,他的父親雖然還健在,可是當父子相見時,詩人得到的卻是冷談的嘲諷與嚴實的棍棒。很明顯,他父親決然地否定了彼此之間的父子關係,甚至還以此為恥辱。於是,詩人對於社會帶著矛盾的反叛和報復也得到了深刻的緣由,那便是對於缺少父愛之傷口的異化的撫慰。與此同時,老闆娘對於她那弱智的兒子而言實際上也是一個“替代”的父親,因為懦弱的生父在孩子出生時就因為其弱智而逃離了。而那個酷愛油漆的兒子一直沉浸在母親的溺愛中,即使到了18歲也依然出於兒童的襁褓時期。至於老闆娘為何走上黑道,影片並沒有交待,但我們有理由推測何其錯位的家庭角色有關。
“…爸爸啊/綠色的光/來自活生生的河蝦…吃冷飯/是一種懲罰……”。影片最後,在詩人清醒而又傷感的吟誦中,三條“失父”的線索最終匯蘢在一起。詩人在紅紅的火焰中以一種父親所期望的方式,“穿越了州省”,實現了在精神上向父親懷抱的回歸。老闆娘的弱智兒子因為與“父親”短暫的分離,在孩童們的一次玩笑中夭折於罪惡的街頭。從某種角度來看,他的死更像是一次命運的安排,當老闆娘抱著渾身撒滿油漆的車夫而留下痛苦的淚水時,同樣年齡、同樣失父、同樣用油漆來包裹自己的車夫幾乎成為他死去兒子的隱喻。而在喪子之痛中良心發現的老闆娘也終於讓車夫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這裡,罪孽、拯救、償還通過“父親”這一主題被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而陳英雄也通過對“失父”孩子遭遇地展露表達了對於自身境遇的一種關照。
“父親”從形而上的理解來看一直都指涉著人類的精神家園。無論是對於因為殖民者入侵而被切斷了與傳統脈連越南,還是對於自小離開祖國,移居海外的陳英雄來講,他們都處於一種“失父”和“尋父”的狀態。能夠通過自己的藝術作品真正融入到一直無法面對的祖國實際上成為陳英雄重獲父愛的一種象徵。因而帶著對於文化的反思和對於當下的凝視,他以一個獨特的切入視角為我們現在越南柔軟而殘酷的絢爛圖景,並以一種對生命意義超越性的理解表達了自己
“去國懷鄉”的人生態度。在這個意義上看,影片最後長鏡頭中詩人肉體的隨火而逝,實際上也是陳英雄自己對於故鄉的一次想像式的靈魂獻祭。
(三)沉默的凝視
失父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失語,而回歸則在相同層面上意味著異質文化的交融。或許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三輪車夫》中人物大都是沉默的。車夫在沉默中走向犯罪;姐姐一邊哭泣著出賣自己,一邊無怨無悔地愛著詩人;而詩人則在沉默中痛苦,即使最後的自焚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其它像爺爺、妹妹、甚至是老闆娘也都是在默默地生活和等待。這種沉默自然是第三世界在“後殖民時代”話語喪失的體現。然而,陳英雄的沉默背後卻蘊藏著巨大的生命能量。於是車夫用油漆覆蓋了自己,並將自己使用的第一顆子彈留給自己;詩人則在狂暴地殺死了變態嫖客後,用熊熊大火埋葬了自己;溫順無語的姐姐,也終於忍不住爆發了哀慟的哭聲。當然,自省式的頓悟並不能改變未來,導演最後將代表力量和希望的聲音留給了不同年齡的學生和兒童,他只能夠再次借助想像式的期待尋找一直未能夠在越南社會中出現的那曾經帶給人們安寧和康定的民族的根,或者說“共同的父親”。
除了表達生活態度以外,沉默也是影像的基本特質。它在保留時空純粹性地同時,將觀者置於一個等待、思考、感受的位置之上,從而也通過觀眾與影像的同構表達出對於生命意義和生存狀態的感悟與疑問。我們看到的影片中的人物總是孤獨地處在景框內之中,沉默而無所交流;街道上的人流也彷彿是無聲的河流決然而寂寞地流淌;即便是暴力,也是突如其來地發生、無聲無息地結束。在沒有話語減損的畫面背後我們感受到的是一種強大的凝聚力。孤獨的越發地孤獨,殘酷的越發地殘酷,絕望的也越發地絕望。在說與不說,發言與沈默之間,後者顯然擁有更堅決的態度。與黑幫老大唱著民謠在年輕人的頸上劃上一刀相比,詩人在屋頂上紮死了嫖客時的情境顯得更為有力。
當然,影像的沉默就是導演的沉默,因為在影像背後存在的是導演/觀眾/鏡頭三重視點的融合。而導演的沉默則在表達一種心願,一種將對抗性的言語轉變為靜默而深情的注視的心願,一種將二元對立的膨脹情緒轉化為自我審視以及尋求交融的心願。陳英雄的這種願望無疑是強烈的,在影片中他不止一次用詩歌暗示了這種期望。例如,“沒名字的人/沒名字的是河流/沒顏色的是鮮花/芳香撲鼻/萬籟無聲……能否穿州過省重返家園”;又如,“我童年時代的風箏/懷著破滅時的希望/飄浮在半空/心靈敞開/人類安居於大同的世界了”;而在這些詩歌的吟誦過程中,畫面中切入的不是各種兒童的身影,就是純潔素雅的檳榔棕櫚花;除了表達表象背後的詩意以外,同時也說明了這種意願的純潔性。影片中的詩人是聯繫作品和導演的一個通道,而年輕的車夫則是導演自身痛苦靈魂的視覺再現,當他將自己丟置於藍色的油漆中,把塑料袋罩在自己頭上時,那令人心悸的急促呼吸和詩人窒息的寂靜,分明是陳英雄自身的靈魂在掙扎。
陳英雄的努力並沒有得到越南國內太多的認可,《三輪車夫》也因為其與國內民眾不一樣的理解而遭到公開放映的拒絕。但是他在個人特質、人生背景、“跨國”運作、“後殖民”文化語境等因素共同交織的多義性文本中所表現的反思和融匯確實體現了導演對於滄桑塵世的深切關注,正如評論所說,“在陳英雄凌厲的視覺語言中,影片已經深刻地觸及了城鄉交替下人心的跌宕和生命面對時代急速變化時的無奈感”,因而從引起世界的關注這個角度來講,他是成功的。
(四)色彩與用鏡
色彩是《三輪車夫》中最為重要的一種視覺修辭,這種看上去似乎和影片寫實風格相悖的色彩渲染實際上與主題緊密相連的。老闆娘的弱智兒子喜歡向自己身上塗油漆來吸引別人,這種與小孩用哭聲來引起注意相類似的方法實際上是他孤獨無援、渴望交流又無法交流的真實寫照。但是,他的行為除了引起母親的驚恐和責罵外別無其它。這也為他日後的宿命埋下了伏筆。當他終於倒在血泊中,用醒目的紅色引來眾人的注視時,母親只能用一種低訴式的聲音喃喃說道,“我說過什麼,你為何這麼喜歡油漆?你在哪兒找到這種顏色,我們家是不需要這種顏色的。”紅色這是血的顏色,是生命的本色,如果只有用生命的代價才能換來他人的注意,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我不知道陳英雄是否有意通過這種方式暗示在西方優越視點下第三世界的文化困境,但他無疑表達了某種強烈的感傷。
弱智兒子的顏色與車夫用藍漆來澆灌自己是對應的,但油漆對於車夫而言卻是一種逃避自我的手段。他在藥物的迷幻作用下不斷地捲縮,這是他在自身的罪孽和現實的腐爛面前自我放逐的一種方式,是他渴望逃遁沉重人生的迫切需求。陰鬱而快速閃動的燈光,沉重而壓抑的大片藍色,勾畫著一種與車夫相同的窒息體驗。但畢竟,我們需要看到希望,因而我們未能在他的身上看見那絢爛的鮮紅。而對於詩人來講,他最後也選擇了紅色作為自己的歸宿,只不過相對於靜止的色彩而言,這種跳躍的火焰更具有涅磐和獻祭的意味。
至於影片的拍攝技法,《三輪車夫》對於鏡頭的運用是豐富多元的。在對街頭實景的拍攝時,導演大量運用了追踪地長鏡拍攝、懸空拍攝和俯拍,並通過必要的急速切換來表現街市的浮躁與混亂;在拍攝人物的內心狀態時,則較多使用手提攝影機近距、晃動的拍攝手法,配合逼真躍動的光效,以表現他們的痛苦與掙扎。從整體上看,陳英雄的用鏡寫實與抒情並置,對比強烈鮮明,節奏緩急相間,並通過對金魚、漏電的開關,殺戮時的殘酷與冷漠,突然留下的鼻血,吟唱的歌謠等情境的重複拍攝與疊化在強調影片中變化、不安全、和迷亂的感覺同時,在鏡頭內部構建一種內在的隱喻和詩情。比如,詩人每次處於矛盾與掙扎中時都會忍不住流鼻血,這實際上隱喻了潛藏在他內心的道德審視。又如,影片中多次出現的低沉而傷感的歌謠吟唱,在一個藝術的層面表達了主人公們漂泊無疑的悲涼心態。
其中,有一組鏡頭令人深省。當姐姐在詩人的居所進行第二次性交易時,鏡頭變得緩慢而精緻,對於細節的溫柔雕刻讓我們感覺到一種安詳的詩意。而此時在對面車夫的房間裡,首次進行非法活動的車夫正在為眾人的誇讚而沾沾自喜。導演通過一個起自於姐姐的穿越街道的長鏡頭將姐弟兩人所處的空間聯繫了起來,而在鏡頭的滑動中我們看到站立在兩樓之間若有所思的詩人。這組鏡頭的運用巧妙地點出了三者之間的聯繫。姐弟倆被詩人分置在相對的空間裡,分別誘使他們從事非法的勾當,他似乎是罪惡地源頭。但同時詩人所表現出的憂鬱與矛盾對似乎預示著他作為詩人和黑幫頭目兩個自我間的對抗與掙扎,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詩人的痛苦與死亡。當然,類似的鏡頭還有很多,這裡不作贅述。
轉載自
http://i.mtime.com/questions/blog/370075/